佛教与人生 人生需要的佛法
发布时间:2022-10-25 11:11:52作者:地藏经讲解网人生需要的佛法
佛陀设教的宗旨,在乎普度众生,而在这所度的众生中,尤以人类为救度对象的中心,因此佛陀是为人生而说法,佛法是为人生所需要的;人生的许多痛苦,也惟有依佛法修行,才可以解除。这在研究过佛学的人,是没有什异议的;可是许多未曾读过佛书的人,往往只看到有一些佛教徒不合佛法的外表和行为,或以为佛教是迷信的,与社会不利的。现在为要纠正这些对佛教抱著错误的观念,我要把佛教的道理分四项,略为说明:
(一)佛法是信智并重的
每一个宗教,首先要著重信仰,如果没有了信仰,那就不能成为一个宗教。佛教是属於宗教的,因它与其他宗教一样的著重信仰;同时佛教也可以说是非宗教的,因它有与普通一般宗教说法不同的超低性。比如佛教重信仰,是不错的;而它尤重理智,是把信仰建筑在理智上的,否则信仰便会变成盲信,迷信。所以大智度论说:「佛法大海,信为能入,智为能度」。在这里见得只有信,没有智,是不能了彻人生真谛的,即使学佛也难以获得究竟离苦得乐的;这就是佛教与其他「因信得救」的,只偏重信仰的宗教不同的地方。
佛教是智慧的宗教,可是这种智慧不是普通一般的知识。知识是外向的,从外面的学习经验得来的,是有限量的,也不是统统都是正确的;佛法的智慧是内向的,是向内在掘发出来的,是无限的,正确的。这种智慧是必须依修戒而生定,由定功而开发出来的,它是经得起时代一切学术的考验,其合理和超越性,在世间一般宗教哲学中,是不易找得到的。由智慧契证诸法的真理,才能产生真知灼见,为古今中外的文化学者所赞赏。如中国的国学大师章太炎说:「佛教的理论,使上智人不能不信,佛教的戒律,使下愚人不能不信,通彻上下,这是最可用的。」康有为先生说:「仙学太粗,其微言奥理无多,令人醉心者有限;不若佛学之博大精微,至於言语道断,心行路绝,虽有圣哲,无所措手,其所包容,尤为深远。」英国哲人罗素则说:「各宗教中我所赞同者为佛教。」佛教如果不具有甚深的智慧和崇高的学理,那会使一般时代的哲人,心折如此呢!
(二)佛法是标本兼治的
佛教的智慧,分有真实智和方便智。真实智是体,方便智是用,从真智的本体上,生起种种摄化有情的方便作用,就是佛教福利社会的道德风化。我们知道社会是群治的,由於农、工、商、学、兵以及宗教各界的人士,各司其职,各尽其能,才能促进社会的安定和繁荣;可是今日的社会,人心如江河日下,淳源凉薄,风化不良,杀盗淫妄,肆无忌惮,虽绳之以国家的法律,只能治之已然,不能防犯未然,只能治标,不能治本,惟有佛教的戒法,才能净化人心,澄本清源,足以移风易俗,树立良模。
佛教的基木戒律,在於五戒,是人伦的正法,近於儒家的五常。一不杀生是仁,儒家所谓「仁民爱物」,或「民胞物与」;二不偷盗是义,所谓「路不拾遗」,「弗义之财不取」;三不邪淫是礼,所谓「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」;四不妄语是信,所谓「民无信不立」,「人而无信,不知其可也」;五不饮酒是智,所谓「酒能乱性败德」,「酒不醉人人自醉」,亦如「色不迷人人自迷」。酒能导色,故宜戒绝。五戒的性质与五常相同,而作法有异,儒家的五常重在理论,佛教的五戒制为必行的规条,不行则犯,名之破戒,有应得之罪业,受应得的果报,故凡受其戒者,莫不遵行,惟恐有犯。如果人人各安其位,各守其戒,则一人如此一人治,一家如此一家治,一国如此一国治,全世界人如此,则全世界亦国治天下平了。因此如有五戒治其本,加以法律治其末,标本兼治,则社会大同,人民坐享其利,欲世界不太平而不可得了。
(三)佛法是冤亲平等的
我们人类在平日互相接触的关系上,不免有厚彼薄此,或爱此憎彼的协调与不协调两种现象的产生,这即所谓冤家与亲家的不同。为亲家的日日相见,自然欢喜;最难堪的是冤家狭路相逢,分外眼红。这样由小冤家变成大冤家,或由少人的冤家变成多人的冤家,弄到家庭不睦,社会不宁,也成为国家乃至世界发生斗争的导火线,是不可忽视的事实。人类的冤亲关系,必须要透过佛理,才得协调,而免除过与不及的弊病。佛法体验到人生应要冤亲平等看待,是有其两个深切的理由:一是佛陀曾彻悟到人生的共同原理,在於共同的佛性。这个共同的佛性是人人具足,个个不无,而且又是「在凡不减,在圣不增」。就在这共同具有的佛性上,体知大地众生,不论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,甚至有情与无情,动物与植物,都是同体的;既然是同体的,还分什亲疏适莫?说什「仇者快而亲者怨」?如果悟知众生同体而强分亲疏,自己平心一想,亦不免哑然失笑了!二是佛陀从天眼智,观察众生是死此生彼,轮回不息,都曾互相做过父母兄弟,姐妹眷属的亲戚关系;以宿命智了彻众生界过去无始以来,一切人事过从,有更亲密更深切的关系。就在这种更亲密更深切的关系上,不但光是人类,就是对人类以外的其他动物,亦要建立起这亲切的关系。这样观想,谁肯把自己的亲人当作冤家来仇视?谁肯举刀残杀自己同体的众生?杀机既息,则一切冤家都变成亲家,内在不再发生怨憎瞠恨的心理,外界的家庭或社会斗争亦不存在,人类自然趋于和乐了。佛陀不但是理论的发现者,亦是理论的实践者。如佛陀在世之时,因为过去世未修菩萨道时与提婆达多结下怨恨,所以提婆达多时时想害佛报仇,时时来找佛陀的麻烦,跟佛陀过不去;可是佛陀并没有对他感到麻烦或烦恼,反之还对他表示亲切的好感,时时向大家说提婆达多是他的好朋友,善知识,由於提婆达多多生的逼拶兴鼓励,他的道业精进勇猛,提早得到越级的成功。就是那位与提婆达多做朋友的阿世王,受了提婆达多的唆使,不只毒害了父母,而且跟佛陀也有过不去的地方,可是佛陀对他也没有半点仇视,当他恶报现前,受到身患毒疮的痛苦,向佛陀忏悔,佛陀还是慈光摄被,使他毒疮平复,恢复了健康。这些,都是证明佛陀不光是在理论上说冤亲平等,而是在行动的事实上实现了冤亲平等。
(四)佛法是自他两利的
普通一般人的感觉,看见佛教徒入山或闭起门来用功,都以为佛教徒是消极厌世而自利的。其实呢,入山或闭门自作工夫,正是为入世利人做预备。所谓「以出世的精神,做入世的事业」,恰可以表达这个意思。
佛教的宗旨,在「诸恶莫作,众善奉行」;诸恶不做,是消极的自利,众善奉行,就是积极的利他。所谓自他两利,这不是很明显的证明吗?为什要硬说佛教是消极厌世而自利的呢?同时佛教行善的定义是:对於所行的善事,必须於己於人都有利的,才叫做善;如果於自己有利,於他人无利或有害的,就不能叫做善。又所作的善事,必须於现世有益,於来世亦有益的,才叫做善;如果只是目前有益的,而将来无益的,亦不能叫做彻底的善。这样来看佛教的为善,就是自他两利的标准的行善。所以学者梁启超居士说:「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,乃兼善而非独善,乃入世而非厌世」。又说:「佛教之最大纲领,日悲智双修,自初发心以迄成佛,~?转迷成悟为一大事业。」修智以求转迷成悟,是自利的事业;修悲救济众苦,就是利他的大事业。如此,一个真正懂得佛理,能行佛事的佛教徒,就是人生自他两利的事业专家,相信谁也不敢说他是消极自利的逃世者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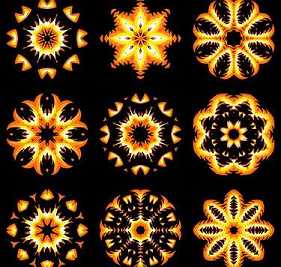
佛教的大乘行者,他们所作的事业,不但是自他两利,而且是利他重於自利,为人急於为己。孙中山先生曾说:「佛教以牺牲为主义,救济众生。」即是有见於此而云然。因为大乘行者的菩萨,他的发心修行善事,见苦必救,有求必应,你如果真有需要他的地方,他不但身外的财物可以布施给你,满你所愿,甚至自己宝贵的妻孥和生命,亦可以施献於你,真是「难行能行,难作能作」。而且他的布施为善,还是观空心境,不挟企图,所谓「度尽一切众生,而不见有一众生为我所度」,不杂丝毫功利观念。像儒家所说的「杀身成仁,舍生取义」,亦都是可歌可泣的牺牲为人的行动,如果其中不存为功为忠的有得念头,或贪「千秋万岁名,寂寞身後事」的英雄浮名,那都可视为牺牲为众的大菩萨了。
中国在东晋时代有个叫邓攸的,他在石勒兵到,怆惶弃家逃走,因其弟早亡,特全其侄,继其香火,而把自己的儿子系在树上而不顾。为救侄儿,牺牲了自己的儿子,可以说已做到了无我的境界。这在佛教看来,也已成了舍己为人的利他行者,因此,世间一切「先天下之忧而忧,後天下之乐而乐」的贤者,莫非是菩萨化世的大乘行者。佛教得名牺牲主义,其价值就在乎大乘菩萨所表现的积极救世的利他精神。
人生一世,只有数十寒暑,不坚常的肉体,终归要坏灭的;而不坏灭的是精神的生命,所谓立功、立德、立言,是人生的三不朽。大乘行者的作为,就是人生三不朽的代表。人生必须在数十寒暑的短促时间中争取生命史上有价值的东西,才不辜负人生,失去人生生存的意义。现在从佛教是智信并重,标本兼治,冤亲平等,自他两利的四个要点上看,人生如要过比较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,少不了要向大乘行者学习看齐;或惟有大乘行者的救世行径,才是人生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憧憬与追求!
佛纪二五一二年七月十五日於槟城三慧讲堂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