娘,还能饭否?
发布时间:2024-11-03 03:18:57作者:地藏经讲解网娘,还能饭否?
那些年在乡里,我娘饭量大是出了名的。我娘说,总感觉肚里肠子是空荡荡的。
我娘生下我那年,平时吝啬的奶奶大发善心,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,顶住压力杀了一只母鸡,炖了蘑菇给我娘发奶水。全家人,眼巴巴望着月子里的娘吃鸡,我娘几乎是面带凶相地啃鸡骨头,甚至把鸡骨头也嚼下去吃了,她听我爹说,吃了鸡骨头补钙。
我娘忆苦思甜时说,那些年啊,肚里油水太少,三十多岁了还尿床。有一年,生产队里病死了一头猪,夜里掩埋了。第二天早晨,胆大的人又把死猪从土里刨出来,愿意吃的人,就去提上一块肉回来打打牙祭。我娘就是生产队里吃死猪肉的人,她自己吃,把全家人也带上吃了,结果没事,晚上睡得很香,大人小孩都没尿床。
我娘苦啊,是家里主要劳动力。我爹在城里当干部,星期天回来指导一下农业生产,也是在田边指手画脚的,有时念念上面文件,说一些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之类的冠冕堂皇话。有次把我娘惹火了,娘发火说:“形势大好,大好,啥时候把肚子填饱啊!”让我爹很无趣,尴尬地离开。
我娘脚小,走路却是呼呼生风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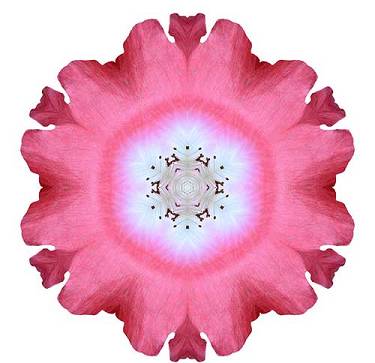
在乡下,农人吃饭都是用土碗,土碗是当地窑里烧出来的。土碗很大,我娘捧着土碗哧溜哧溜扒饭时,我依稀记得一个土碗把她托起的整个手掌都给盖住了。我娘和那些乡人,托着一个土碗,随便在村前黄葛树下一蹲,或盘腿在地,边拉家常边扒饭,往往是吃着碗里的,瞧着锅里的,一大家子人,吃饭像打仗。我现在还记得,娘用锅铲刮铁锅时的刺耳声音,那声音让我想磨牙。
我进城那年,娘塞给我一个黑不溜秋的土碗。娘说,到了城里,就用这饭碗,装得多。
当然,我没用土碗,很快扔进了垃圾堆。娘五十八岁那年进了城,是我给她下跪求了情,并保证,今后她死了还是埋在老家。她带来了土碗,坚持用土碗吃饭,只要有白米饭,一样菜也没有,照样吧唧吧唧吃得很香。
起初几年,我娘的饭量还是没减多少。但过了六十五岁,我娘的饭量,大减了,带来的土碗,换成了比酒杯大不了多少的青花瓷碗。
去年,我娘六十九岁生日,我看见她把头埋在小碗里扒饭,像鸭子吞食一样,喉头猛地抽搐了几下。我给娘夹了几坨鱼,她竟被鱼刺卡住了,憋得满眼是泪。
一瞬间,我才明白,我娘在老去,从前用大土碗哧溜哧溜扒拉着饭的娘,一顿吃上几大碗饭的娘,再也回不来了。
我娘,多希望您每顿饭,还能吃上一大土碗。我娘,而今我想,您的儿子,在您剩下的时光,一年之中,多陪陪您吃上几顿饭,我要和那些纯粹的酒肉朋友慢慢绝交。



